“三和青年”的丧与抵抗:做一天玩三天 一千块过一个月
2020-09-20 07:56:47
来源:
网络综合
刚到深圳三和人力市场周围的城中村小巷子时,林凯玄兜兜转转数次,才终于鼓起勇气向一个旅店房东询价。房东上下打量他一通后,拒绝了。他看了一下周围的务工者,觉察出自己被拒绝的缘由,便立马去小商店买了一个水桶,在里面放了一些生活必需品,背上双肩包,再次走进那条小巷。这一次,终于有房东主动上前来打招呼。
就这样,林凯玄跟着房东上了楼,开启了他对“三和青年”的社会调查。出现在他眼前的房间,床板发霉,席子黏糊糊,还有蚂蚁、蟑螂、臭虫爬来爬去。空气中,汗臭夹杂着脚臭,再混合厕所里的尿骚味,令人作呕。这个“90后”男生的第一反应是拔脚就走,但想到自己的研究计划,经过一番心理斗争,还是决定留下来,过上了与“三和青年”同吃同住的日子。之后半年,为了和各类“三和青年”打成一片,他辗转了10个“三和青年”聚集的旅店,躺过15元一晚的床位,住过20元一晚的“棺材房”,也住过30元一晚的单间,还拿着硬纸板睡过大街。
“三和青年”是一群在深圳三和人力市场找工作的年轻农民工。他们居住在人才市场周围的城中村里,以“日结”(每天结算报酬的工作)为生,常常是“做一天玩三天”。这里有非常廉价的旅馆、网吧和杂货铺,许多人一天只吃一碗五块钱的面条,喝2元一大瓶的水,生存成本很低。与追求勤奋工作、品质生活的主流群体不同,“三和青年”过一天算一天,对身无分文、失去工作的状态没有多少不安,彼此之间经常以此调侃,甚至鄙视有稳定工作的人。“三和大神”则是“三和青年”的升级版,他们似乎是完全放弃了自己,随时可以睡倒在潮湿的巷子里。
“三和大神”出名,最早是因为NHK的一部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在这部拍摄于2018年的纪录片里,年轻的农民工在繁华都市里挣扎着。他们对“通过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早已失去希望,只能过一天是一天,只要不挨饿就坚决不干活。片中一个青年说的话——“一百块钱干十几个小时,我说了,宁愿饿死也不干”——被很多人视为是青年抵抗“工厂文化”的标志。
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看来,“三和青年”是中国目前为止能够观察到的最接近于美国黑人社区和巴西贫民窟的底层社会。因为多方面的原因,此前,国内学界对“三和青年”这个群体始终没有相关研究专著,以“关心底层”为底色的社会学也没有专门的研究,网络上的传闻又往往以猎奇的视角去寻找这个群体的极端之处。
最近出版的《岂不怀归》是第一部针对“三和青年”的调查报告。两位学者,田丰和他的硕士研究生林凯玄,试图尽可能挣脱理论束缚,不带预设,以白描的手法还原真实的“三和青年”。这项研究没有申请任何科研经费,出版过程也是历经磨难。经过反复努力,虽然损失了一部分内容,这本书还是在成稿17个月以后出版了。出版至今两个月,《岂不怀归》已经加印两次,在当当、京东等网络图书平台上的销量都名列前茅。
还原真实的“三和青年”
在三和,快递、工地和保安是最常见的“日结”。在工地干活收入最高,但因为劳动强度大,是最不受待见的。“三和青年”喜欢会场保安的工作,即便收入不高,一天130~160元之间,但胜在舒心悠闲。“卧底”那段时间,林凯玄曾去工地搬砖、提灰,也到饭店做过临时服务员。他认为,一起抢“日结”,是最能加深“三和青年”彼此情感连接的方式。
就像林凯玄第一次投宿被拒所预示的,这里的文化与外部是有明显区隔的。要融入这里,除了一起做“日结”外,林凯玄还需要做很多改变,比如外形,“拖鞋、牛仔短裤、一件短袖成为我的经常性穿着”。他曾有近一个月没有清洗牛仔裤,每天随地而坐,甚至分不清是深蓝还是灰蓝色,T恤上也沾满泥土,长时间不洗头、不洗澡的邋遢形象甚至让其他“三和青年”都开始嫌弃他。
还有吃饭,一块钱一包的零食、两块钱一碗的粉和瓶装水,成了林凯玄的主要食物。“三和青年”虽然兜里钱很少,但当同伴身无分文的时候,他们会拿出仅有的几块钱请对方吃饭。
林凯玄觉得,衡量“三和青年”是否信任他的标准就是,他们在“日结”回来以后主动请他吃饭。
“三和”的消费相当低廉。一块西瓜1元,一碗面5元,一瓶水2元,还有专卖二手衣物的摊贩,粗略估算,一个人一个月最低需要1200元花费。只要偶尔做做“日结”,活下来的确不是难事。那里又有热闹轻松的环境和包容的氛围,这会使人滋生惰性。“三和青年”与外界格格不入的地方也正在于此,他们的生活漫无目的,既不赚钱,也不返乡。不少人还会讥笑那些兢兢业业的务工青年,把流水线小工说成是“富士康奴隶”。
更能反映“三和青年”精神状态的是语言。“如大神、挂逼、叼毛、睡大街等,也有一些与工作和娱乐联系的词汇,如做法人、百家乐、有衣库等,如果不能深入三和青年群体之中,难以全面理解这些词汇的深刻含义。”林凯玄说。
这才是三和大神的日常,抵押手机换钱过日子(来源:~)
与“三和青年”接触了半年,林凯玄觉得,之前在网上看到的文章有夸大之嫌:“把少量‘三和大神’的状态辐射到三和的每一个青年身上,把一些影响因素归结为青年个人。”事实上,真正完全放弃自己的“三和大神”只是很少一部分,大部分青年都是在“日结”与“游荡”之间来回纠结。有工作的时候,可以奢侈一下,花30元住单人间,洗完澡,躺一会儿,没钱了,就只能一天吃一顿饭,花一块钱买一个硬纸板,睡在街头。
林凯玄说,他在“三和青年”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出生在河南农村,家里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力耕作,劳作辛苦,吃住不好。小学升初中时,他也曾处在辍学边缘,在家人的鼓励和自己的努力下才继续学业,避免了外出务工的命运。大学期间,他做过与“日结”类似的暑期工,对在三和的生活,他的感受是“再辛苦,也觉得可以忍受”。
一直到调研结束,“三和青年”都不知道林凯玄的真实身份,“或许他们觉得一个来自北京的学生不可能做得那么彻底”。
“三和青年”的复杂成因
每一个 “三和青年”背后,都有一个故乡,只是,即便再穷,他们都没有选择回到那里。书里没有对“三和青年”家乡的直接描述,读者只能在离家者的话语里看到一个个模糊的影子。
一些青年在提到家乡时,说自己在外面打工挣不到钱,回家十分丢脸,也不愿意面对家人催婚的压力。他们虽然人手一部手机,整日在手机上付费、休闲、抢“日结”,却很少主动与家人联系,更不会透露自己的现状。
这里头,一个叫“广西酒鬼”的人的经历有一定的典型性。“酒鬼”结过婚,育有一儿一女,孩子由家中父亲照料。他初中就辍学外出打工,资助弟弟、妹妹上学。现在,弟弟和妹妹在深圳都有了稳定的工作,“酒鬼”却过得相当落魄。他曾因飞车抢劫被抓,虽说家里花了仅有的十几万把他“赎”了出来,但妻子从此远走高飞,乡里人也都知道了他的案底。来到“三和”以后,他除了在工地做“日结”,就是喝酒、赌博以排解内心郁结。他的弟弟、妹妹就住在三和人力市场附近,但他从来也不向他们求助,他说,“有钱、有工作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容易办,什么话都可以说,混得不好了,即使别人没有嘲笑你,也总感觉自己失败,没有脸见人。”他从不回家,也是怕父亲和孩子们看不起他,怕乡邻们说闲话。
台湾节目:深圳“三和大神”,在“魔幻部落”里失去狼性的青年!(来源:~)
田丰分析,“三和青年”是第二代农民工中产生的特有现象。相比于第一代农民工,这代人家庭负担更轻,至少不是全家人的经济支柱。他们中的很多人曾是留守儿童,家庭观念淡漠,对父母在情感上并不依赖。他们从小从网络上看到城市人生活的状态,对生活的期许更高,权利意识更强,对不公平也更敏感。一旦遭受不公,他们不会像父辈那样忍气吞声,而是主动维权,但又缺乏维权所需要的手段,这就使得他们采用一种新的抗争方式:在大城市里“混吃等死”。在书的前言部分,田丰写道:“在访谈中,三和青年经常说的一个道理就是:不想工作的原因是不愿意被剥削、被克扣、被歧视。”
田丰和林凯玄都认为,“三和青年”的成因是很复杂的,很难仅仅归结到青年个人身上,这背后凝结了经济社会制度、城市管理模式、代际文化差异等多方面因素。城市无法落脚,家乡也很难容纳他们,这些青年的归宿在哪里?“岂不怀归”,这个取自《诗经》的书名,表达的正是两位社会学学者的追问。
相关推荐
三和青年:我们只能靠跳楼活着
编者按:在深圳龙华的三和人力市场,有一群被称为“三和大神”的九零后、零零后农民工。他们依靠日结工作而生活,“干一天玩三天”,吃最便宜的面食,住十几元一晚的旅店,有钱就去网吧里待到天明,没钱就睡在大街上。
三和青年这种“得过且过”的生存状态是怎样形成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林凯玄,在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的指导下,去到当地田野调查,每天跟三和青年一起吃饭、住宿、去人才市场,白天观察,夜晚记录和整理。师生二人共同完成了《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一书,用白描式的研究手法,还原三和青年真实的生存状态,展现他们既无法融入城市、又不想回到农村的双重困境。
在田丰和林凯玄看来,三和青年“混吃等死”的表现,其实也是一种无奈的反抗,他们期望获得有保障又自由的工作,但又没有能力实现。而深圳的经济社会环境为他们的低成本生存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尽管三和青年挣钱养家的压力小,却也面临着和一般打工者类似的困境——缺乏应对劳资纠纷的办法。由于经常被黑中介、黑工厂“坑”,跳楼成了一种逼不得已的表演和应对手段。以下内容摘自《岂不怀归》,该书已由新经典/海豚出版社于近日出版。
文 | 田丰 林凯玄
1
“兄弟别去,那是黑厂,我们去上网。”这是三和贴吧中流行的一句话,也是很多青年在经历过进“黑厂”、与“黑中介”打交道后总结的经验,还是“有经验”的三和青年对初来乍到的年轻人的善意提醒。“黑厂”是很多青年选择不进厂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按照他们的描述,“黑厂”具有下列特征:管理严格,无福利保障,经常加班,无故克扣工时、工钱,不签订劳动合同,住宿环境和工作条件差。
与“黑厂”相关联的另一个概念是“黑中介”,指的是压榨三和青年的劳动成果、层层克扣工资、骗取务工青年身份证、诱骗务工者进入“黑厂”的中介公司。“黑厂”与“黑中介”是三和青年对深圳周边广泛存在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中介公司的一种蔑称,体现出三和青年与工厂和中介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些人力公司以蒙骗的方式,夸大工厂的优越条件,就是为了招到更多的人,获得更多的提成,至于务工者在工厂里究竟境遇如何,中介并不关心。务工者受骗后回到三和与中介理论显然于事无补,即便报警也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务工者若干次受骗后,为了能够维系生活、等待合适的工作而留在三和做日结,也就成了三和青年中的一员。
尽管三和青年与“黑中介”的关系变得紧张,在很多情况下却又逃不脱中介的掌控,毕竟中介公司掌握着就业资源。即使做临时工也必然受到人力公司的“压榨”,所以又有很多三和青年把挂逼的原因归咎于“黑中介”的压榨。
三和青年和“黑中介”之间的矛盾一直在积聚,这种矛盾虽然很少直接表露,却会在三和青年遭遇不可忍受的情况时迸发出来,比如没钱吃饭、身份证被骗的三和青年会不顾一切地与“黑中介”爆发冲突。据说,一家极为过分地克扣和欺骗三和青年的“黑中介”一度引发他们之间的肢体冲突。在众多三和青年的围观与声援下,中介公司的老板和员工毫无还手之力,藏在办公室里不敢出来。
在受到举报而被查封那段时间里,“黑中介”租赁的办公场所夜间还遭到三和青年的打砸和火烧。当然,这是极为罕见的三和青年占据优势的例子,绝大多数情况下,占便宜的还是人力公司,三和青年只能默默吞下苦果。
与招聘工厂岗位的中介相比,三和青年和日结的中介关系则要缓和得多。由于外来招工者到三和招日结的数量和时间都不固定,做不到每天招人,即便招人每次数量也较少;所以,在三和垄断日结工作的“黑中介”主要是由中介公司的人来兼职。比如招快递日结和保安日结的“海新四大金刚”,白天就是在中介公司招常规工人。由于做日结是最重要的谋生手段,所以,即使“黑中介”克扣工资,为了生存,三和青年也还必须依赖他们。
二者之间的矛盾不会那么明显,有时还展露出温和的一面。有的青年通过“黑中介”大帅的通融,借钱买一双鞋才得以出去做日结,他们之间既潜藏着矛盾,又相互依存。
实际上,他们很难真正有什么手段和中介较劲,更多时候只停留在“口诛”阶段。一次,三和青年发现手中免费领取的书讲的是因果报应,便说笑道:“应该把这些书发给那些中介,他们太黑了,赚的钱太多,欺骗‘三和大神’要遭雷劈。”这虽是一句说笑,却显示出他们对“黑中介”既愤怒又无奈,常常私下谩骂和背后指责。
三和青年处于社会底层。在关系资源不足、维权能力弱小、正式途径难以妥善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通过把事情推向极端的发声方式,采取非正式的途径解决问题,比如说能够引起轰动的跳楼。
2
上午的三和人流涌动,数以千计的外来务工者聚集在各个人力公司大厅寻找合适的工作岗位。在这个“繁忙”的时段,只见大批务工青年快速地聚集在一家人力公司门口,他们不是奔着良好工作条件和较高薪资待遇的岗位而来,而是被坐在三楼窗户外的一位青年所吸引。
一句“有人要跳楼了”,打破了无精打采的“正常”生活,他们纷纷走出彩票店、小超市和小巷子。不到10分钟,至少有三四百人在楼下仰头围观。此刻,跳楼青年的一举一动都成为三和的焦点,了解一些内情的人也开始七嘴八舌地炫耀自己的谈资。
事件的起因是,跳楼青年通过一家中介(人力公司)的介绍,选择了一份工期为15天的临时工作,按照约定,做满工期就可以以最高小时工资标准结算薪资,回到三和与中介结算工钱。跳楼青年回来后,先不说工厂内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没有达到中介所夸大的标准,在工资结算方面也未按照所约定的最高小时工资标准发放。而中介给出的解释是,工厂给他们的工时工资就是这么少。可想而知,是中介克扣了工时,又在工资标准上欺负跳楼青年。
跳楼青年自然不肯吃亏,与中介理论,因为没有任何劳务合同或书面证明,也没有工厂内的工时记录,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跳楼青年被“黑”,而中介的蛮横无理更加剧了冲突。跳楼青年并不甘心,情急之下做出了跳楼的选择。他通过二楼的公厕爬到三楼,坐在一扇窗户外面,做出要跳楼的姿势以吸引市场管理者、中介和务工者的注意,目的显然是期待着有利于自己的处理结果出现。
随着三和青年和务工者的迅速聚集,伴随着他们兴奋的喊叫声,市场管理人员和中介都赶过来查看情况,并迅速报警,交由警察处理。一旦发生跳楼事件,市场和中介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随后市场的几位协警也前来关注情况变化,对于这样的事件他们无能为力,只好控制住围观的三和青年和务工者,让他们不要靠近,以免出现更加混乱的状况。虽未拉出警戒线,却也预留出一些警戒空间。
跳楼青年坐在窗边,不停地向下探头观望情况,并时不时地做出想要跳下来的动作,引得楼下聚集的人群议论纷纷。三和青年幸灾乐祸地关注着跳楼青年的一举一动、不时地有人躲在人群中大喊一声“跳下来”。而内圈的协警立刻喊道:“谁叫的?出了问题全是你的责任。”跳楼青年一直不为所动,他在等待更好的处理方式和结果,这也说明,他并没有跳楼的想法,他是在寻找解决问题的非正规途径。
终于有一位穿着正规警服、佩戴着警号的警察来到现场,他先是了解情况、布置任务,协调其他部门帮忙。不久,紧急救护人员和消防队也来了,事态进一步扩大,就连在网吧里厮混、不愿意出去做工的青年也被叫喊声吸引到现场。“很长时间没出现过这样的场面。”一位刚从网吧出来、眼里布满血丝的青年感叹道。
当所有可能发生的隐患和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全部就位,警察也向相关人员了解了事情发生的原因后,接下来就是上楼与跳楼青年谈判,询问他遇到的问题、需要满足的要求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经过协商,跳楼青年同意先下来,到警务室谈判,进一步核实相关情况。随后,看热闹的人都快速散去,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只在吹牛时,才又把这件事津津乐道一番。至少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内,跳楼事件都是他们的主要谈资。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他们对人对事的惯常态度,“唯恐天下不乱”又是他们热衷选择的行为方式。他们围在一起讨论工作时,常提及“黑中介”,跳楼事件则成了佐证“黑中介”不法行为的有力证明。当然,更多的是戏谑的语言,有的人说:“从三楼往下跳肯定摔不死,应该到中国银行大楼上去跳,那样动静才大。”
还有人说:“‘三和大神'这么多,这样的事见怪不怪,真死了也没啥。”更有甚者,拿着地摊上摆卖的弹弓比划着说:“要是昨天你过来,可以拿着弹弓打他,把跳楼的打下来。”有一位年龄稍大的人说了句让人心寒的话:“就是三和的人死光了,我也只会笑哈哈的,不会伤心。”诚然,他们的状态确实很难博得他人的同情,他们对于周围人的死活似乎也不再关注,唯一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存问题。
围绕跳楼事件,也会有一些理性的讨论。有人拿国外劳工保护的案例做对比,讲述国外的工人如何得到工作时间和工资上的保障,而三和青年又是如何受到“黑中介”的剥削压榨。不过他们也找不到解决途径,最终又把问题归结于没有社会资源和技术能力,“自己老老实实工作还被骗,没有能力没有资源,只能继续在这里挂逼”。归根结底,跳楼事件像是一场表演,跳楼青年被“黑中介”坑了之后,缺少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而被迫采用极端手法。
在整个跳楼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跳楼青年从一开始就是想要钱又想要命,在三楼的窗边坐了好久,吸引了大家的关注。而警察上楼之后一直劝说青年保持冷静,只要下来就帮忙解决问题,显然也是害怕事件处理不当,真的出现自杀事件。
关于跳楼青年被带走后的处理结果,有人揣测说:“肯定要挂逼了,这又给三和增添了不好的事。他肯定会被送到救助站,如果有身份证的话可能还会被遣送回老家。”之后据协警等传出的消息说,对跳楼青年给予补偿之后教育一番,就直接放他走了。由于跳楼青年没有受到惩罚,又解决了被“黑中介”坑的问题,这件事情为其他人解决问题提供了参考,三和青年似乎找到了一种可供复制的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也成了他们在无望时寻求救助的一种方法。
不久,三和就再次上演跳楼闹剧,这对于长久待在三和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稀奇,只是每一次发生都会给无聊的生活增添一点乐趣,大家还亲切地称这些跳楼的人为“跳楼哥”。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责任编辑:杨强_NN6027
[责任编辑:RDFG]
责任编辑:RDFG215
关键词:
为您推荐
热门文章
最近更新
-

成都:去医院就诊凭健康码绿码通行 买发烧药不需实名登记
-

小鹏G9获广州自动驾驶路测资格 探索零改装量产Robotaxi新模式
-

竹山县第二中学举行教师节表彰活动
-

专访云生集团创始人李贤威:科技赋能 不确定时代下的确定
-

瞭望|养老保险“一个都不能少”
-
中国银联推出12项助商惠民举措 减费让利相关措施将延续至2024年
-

喜报!社宝科技深圳公司荣获“2021年深圳市人力资源服务行业诚信机构”
-

国际高端家电gorenje引领高品质生活新方式
-

双11狂欢季,优趣汇泰然入局,华丽收官
-

康师傅“急难救助车”深藏情怀与智慧
-

上半年扭亏为盈 优趣汇(02177.HK)核心业务增长稳健
-

连战连捷!国际高端家电gorenje为张雨霏不断突破极限喝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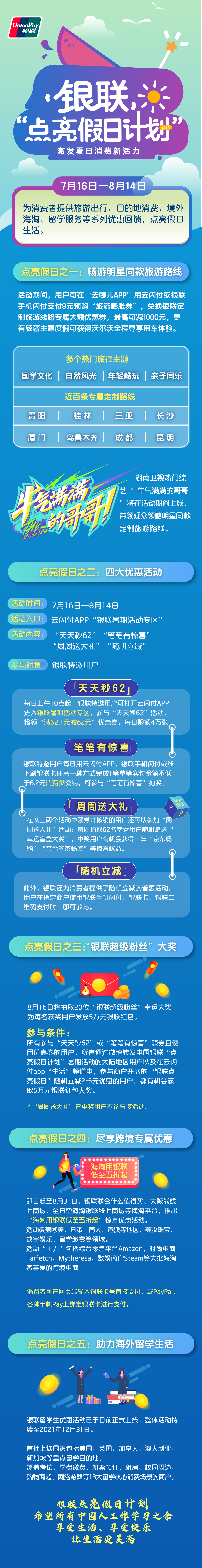
出游宅家好礼不停 银联“点亮假日计划”等你来
-

绯红夜色,传奇揭幕 路易十三焕夜N13特别款全球首发
-
谋事创客省级社区全部建成!
-

决战即将上演!欧洲杯官方合作伙伴gorenje与您共逐冠军
-
筑梦之星履行服务职能,优化青年创业软环境
-

精酿啤酒选雪熊,适合年轻人的酒
-

尝过这款精酿啤酒,我把家里其他啤酒扔了
-
益盟积极拥抱金融科技创新浪潮,为中小个人投资者服务
-

莫比花样动感单车安全性能有保障
-

莫比花样动感单车快乐健身,科学健身
-

各渠道发光发热,红牛持续火热畅销
-

动感单车什么牌子好,莫比设计很贴心
-

行业聚力 支付为民 银联携手商业银行推进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取得积极成效
-

身体清洁大有学问!哈罗闪儿童二合一洗发沐浴露洗出快乐夏日
-
新星宇之悦东郡四期盛大交付 | 匠心之作 美好共鉴
-

夏季出门防晒霜必不可少,哈罗闪的这两款清洁产品更要准备齐全!
-

新星宇控股,高品质房屋迎你回家
-

健康产品迎高光时刻,618荣泰A60指力大师笑傲万元机市场